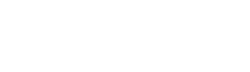提供互联网点播终端服务侵权问题的 另一种解决路径
提供互联网点播终端服务侵权问题的
另一种解决路径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杜昌敏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郭秀刚
内容摘要:酒店等经营场所提供可上网的投影仪、智能电视机等点播终端,供顾客自己操作在互联网上搜索点播观影APP上的视听作品,目前大都被认定为侵犯放映权。此类型的批量维权诉讼在全国数以千计,经营者普遍叫冤,难以服众。法院的判决和公众的普遍认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酒店经营者也几乎不可能通过有效途径事先获得放映权的授权许可。经营者陷入了提供设备即等于侵权的困境。本文提出另一种解决思路,即从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获得”的法律特征上解决此类困境。顾客利用经营者提供的可上网设备自己动手操作点播来自网络的第三方APP上的视听作品时,该行为属于“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他人提供置于互联网的作品,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个环节,不属于放映权的控制范围。因此,解脱了经营者侵犯放映权的困境。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人可向观影APP运营者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这样可以达成多方共赢,社会和谐。
关键词 酒店 技术设备 点播 放映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引言
近几年来,众多名称冠以“文化传媒”的公司,受让大量影视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放映权等著作财产权后,针对“影咖”、酒店等提供专门性或附带的视频点播服务的经营性场所,在全国各地发起数以千计的批量维权诉讼,直引得许多涉诉行业集体反弹,叫屈连天,法院案件数量大幅增长,判决屡有争议。学者也多有发表论文,对涉诉的此类行为构成侵权与否、侵犯的是哪项著作财产权等问题进行论证。
此类被诉的经营性场所在涉及视频点播服务时,所提供、使用的设备,一般都是需要连接互联网的投影仪、机顶盒、智能电视等上网设备,顾客需要通过遥控器操作,通过投影仪或机顶盒下载安装的视频APP上选择点播相关的影视作品。在广大经营者看来,他们就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上网的观影设备而已,在互联网海量的资源库如“爱奇艺”、“优酷”、“腾讯”、“云视听”等应用软件中上网搜索、点播视听作品,都是顾客自己的行为,视听作品也是第三方应用软件提供的,怎么就判定是经营者侵权了呢?广大经营者就觉得自己很冤,很不理解,很难接受。显然,法院的判决,以及一些学者对此类行为构成侵权的分析文章,与广大普通民众的一般常识和普遍认知,以及“朴素的正义观”,存在巨大的反差;如果判定为侵权,则全国数以万计的此类经营场所无一幸免。一项法律的适用和认定侵权的判决,能引起民众的普遍反弹,难以服众,那么,这里一定存在问题,要么是广大民众的认知都出了问题,要么就是法院的判决或者学者们的观点脱离了实际。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目前,此类行为不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已渐趋走向共识,则本文将只从放映权的角度来论述,并以最典型的酒店客房提供互联网点播观影终端为例。
一、 现行法律规范对放映权的规定以及学界和法院判决的观点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项对放映权的定义是: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
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视听作品等的权利。
2018年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5.9条“放映权控制的行为”规定:“被告未经许可将来源于信息网络的电影等作品,通过放映机等设备向现场观众进行公开再现的,构成侵害放映权的行为,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该条规定,直接将放映权控制的范围从之前常见的经营者自己通过服务器、局域网提供片源进行放映,扩大到“来源于信息网络的电影等作品”,即,放映权控制的行为,不论作品的提供来源。
华东政法大学王迁教授,对于此类问题也有论述。其论文《论提供互联网点播终端服务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认为,经营场所提供互联网视听作品点播终端,是创设了一个“现场传播源”,即使顾客是通过“自己动手”在互联网上搜索点播“源于互联网视听服务提供者或他人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中的视听作品”,符合放映权的特征,应属于放映权控制的行为。
而在已经上网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上看,众多判决此类行为构成侵害放映权的案例中,也大多持此观点。如,原告捷成华视网聚(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华市雷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一案【(2022)浙民终1050号】,一审判决认定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二审改判认定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构成侵害放映权: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雷火公司系在其酒店提供带有“云视听极光”软件的智能投影仪,使得入住者能够播放已经通过“云视听极光”软件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作品,因此,雷火公司并未实施将涉案电影置于信息网络中的行为,其仅是通过能够联网的技术设备向入住者再现已然置于信息网络中的涉案电影,故雷火公司实施的行为属于放映行为。该判决观点具有代表性。
二、 经营业者的困境
全国的酒店行业正处于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
按照以上的观点,则似乎变成了“经营场所提供联网观影设备就等于侵害放映权”,简而言之就是:“提供设备=提供视听作品的点播=侵权”。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法院诉讼的、主要以两三家文化传播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数以千计的此类案件,正在大规模的往这个方向前进。[1]
于是,酒店行业经营者的困境就来了:一方面要提升和丰富酒店的服务品质和服务内容,在客房里安装使用接入互联网的智能电视、机顶盒、投影仪等,以供顾客自己上网点播视听作品,增强顾客的住宿体验;但是,另一方面,按照上述侵权的认定逻辑,在事先未获视听作品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客房里提供了此类观影设备,就构成了侵权,而此种侵权的可能,是面对互联网上无以计数的海量的并且无法预见的视听作品的侵权。
那么想要事先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就遇到一个现实问题,通过什么渠道?向谁?去获得互联网上的海量的作品的授权许可?中国少数的几个音乐、音像以及电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显然只代表了少部分的作品,而更大量的作品是没有有效的途径去获得许可的。可以说,事先获得授权许可,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即使可以穷尽一切可能,其代价将是酒店所无法承受的。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8年颁布实施的《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显然无法适用到酒店行业[2]。KTV侵犯放映权有可解决途径,就是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每年按照标准缴交许可使用费,获得一揽子许可,并获得兜底的保护。但酒店经营者显然没有此类渠道。
那最终,就只能是两种结局:要么酒店干脆就拆除此类互联网观影设备,降低服务品质,回归到传统电视机的年代,这显然是对酒店行业,对此类设备的生产销售行业,造成发展上的巨大阻碍;要么就冒着“侵权”的危险放任经营,随时准备应对一场又一场的侵权诉讼。
这显然是酒店行业经营者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王迁教授的文章也只论述到了侵权认定问题,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解决此类普遍侵权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著作权法》对放映权的规定需要注意实施主体的问题
当一项法律的适用,造成一个行业合法经营和发展的困境时,我们是否应该深刻反思我们对这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是否存在误差?
前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5.9条的规定,以及王迁教授那篇文章对于放映权的界定一个原则,即“放映权不论视听作品的来源,无论是放映场所自备的片源还是来源于互联网,都属于放映权规制的范围”。显然,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宽泛而略显模糊的界定。这种界定对于司法实务界影响很大。很多认定侵权成立的判决,都是基于此原则而又模糊的认识而做出的。
而现在,我们需要对此原则而又模糊的界定,回归《著作权法》对于放映权规定的本义,来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项对放映权的定义是: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视听作品等的权利。从汉语语句的基本结构来分析,“放映权是通过技术设备再现作品的权利。”那么,“再现”这个动词,一定是需要一个“主语”来支配它的,在合法行使放映权的情形下,这个“主语”可以是著作权人自己,可以是被许可人等。而反过来,如果是侵权的情形下,则应该是“被控侵权人”未经许可通过技术设备再现作品,即:“被控侵权人”“再现”作品,即为侵犯放映权。显然,再现作品的主体,是被控侵权人。
再说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5.9条的规定,其再现来源于互联网的视听作品的主体是“被告”,即被控侵权人,这是符合上述《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项的本义的。而王迁教授在其文章中进一步论述到,此种通过互联网点播终端点播来源于网络的视听作品,可以是顾客“自己动手”,而不必是被控侵权人“亲自动手”,也同样构成了侵犯放映权。这样一来,则使放映权进入了一个模糊地带。《著作权法》所明确的“被控侵权人”的主语身份就变得不确定起来。在酒店客房的“投影仪”等点播终端上“再现”来源于互联网的视听作品的主体到底是谁?当然不是酒店经营者,而是顾客自己通过网络点播视听作品,此种行为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存在关联?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流程的一个实现环节而不是放映权?我们分两方面来论述之。
酒店客房中提供的连接互联网的投影仪、智能电视机等提供互联网点播终端点播服务的技术设备,其点播操作都是顾客本人,即其从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此类提供视听作品点播服务的观影APP上搜索、点播视听作品。此种点播,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 酒店客房单纯的只提供投影仪等技术设备,该设备上没有事先安装观影APP,或仅
自带可以用于下载安装观影APP的“应用商城”等工具。顾客需要自己操作,先进入互联网,搜索相关的观影APP,下载安装好APP后,再从该APP上点播观看视听作品。
2. 客房中的技术设备,已经事先安装了观影APP,包括该设备自带的以及酒店经营者
购买设备后自己下载安装的。而顾客通过这个事先安装的APP点播视听作品,也包括两种情形,即通过免登录会员即可免费观看,以及需要使用自己的账号密码登录观看。
3. 客房中的技术设备,已经事先安装了观影APP,酒店经营者事先购买了APP的VIP会员,顾客入住后,提供给顾客会员账号密码,以供顾客登录APP点播视听作品。
对于前述第一种情形,当顾客自己使用客房中的技术设备上网搜索和下载安装观影APP,然后再从该APP中点播视听作品。这样,技术设备就确实是只单纯的起到一个上网设备的功能。与所争议的视听作品的提供、放映很难存在任何关联。如果因酒店客房安装使用了可上网的技术设备就判定酒店构成侵犯视听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是放映权,就陷入“提供设备=侵权”的粗暴公式。从《著作权法》对于放映权的规定看,显然,仅提供设备的酒店经营者不能认定为其是“再现”视听作品的主体。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第二、三种情形,相同的是观影APP都是经营者事先下载安装好在观影设备中的。此种情形下,酒店经营者“再现”视听作品的意图很明显,并且与前述第一种情形不同的是,其事先下载的APP,就已经圈定了该APP中的视听作品,无论该APP中的视听作品数量是多么的庞大,但总是被限定的。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种情形下判决经营者构成侵犯放映权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况。上述王迁教授文章的观点中提到的顾客“自己动手”搜索点播网络上的视听作品,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是在哪种情形下,但从其题中之义,应当是指经营者事先下载安装好了观影APP的情形下。此种情形下,虽然是顾客自己动手搜索点播,但却是从经营者事先安装的观影APP上点播的,此时的经营者可被视同于提供了向公众“再现”视听作品的服务,侵犯了放映权。
但是,第一种情形下,如果之前的顾客入住后下载安装了观影APP,其离店后没有删除这个APP,留存在了设备中,对于后续入住的顾客而言,其表象上就变成了这个APP是酒店经营者事先下载安装好在技术设备中供顾客观影的了。那么,此时的酒店经营者将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其将被当作第二三种情形对待,照样被判定侵犯了放映权。因此,实际上只要是酒店经营者在客房中安装使用了可上网的观影设备,都难逃被诉侵权的命运。
但是,如此则又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如果酒店经营者提供上网设备,事先下载安装观影APP,就构成侵犯了放映权。经营者们还是不服气,觉得冤。其都认为,这些观影APP,都是经过审批许可的第三方主体合法经营的,其目的就是供广大的用户观看视听作品的。APP上的作品是这些APP经营者提供,那些起诉被侵权的视听作品,可能是著作权人自己授权许可提供给该APP的,也可能是该APP未经许可擅自收录进去的。如果要打击侵权,也应该是去打击这些APP,而不是终端的经营者。
遍布全国的专门提供上网服务的网吧,其实与酒店客房提供上网设备的情形有可比之处。网吧中也是提供可上网的电脑,电脑有显示屏幕。网吧的电脑上有可能已经提前下载安装了观影的视频软件,也可以通过直接点击网络浏览器上的视频网站目录,打开该视频网站的链接点播观看视听作品。那么,网吧经营者是否也能被判定侵犯了放映权呢?检索裁判文书网,判定网吧侵犯放映权的,几乎没有。
无论是在上述何种情形下被判定侵犯放映权的酒店,几乎不可能通过提前获得网络上海量的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人的放映权的授权许可,从而达到合法经营。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拆除客房里的投影仪等设备,去除让顾客可上网点播视听作品的此项附加的服务。酒店经营者的困境始终存在,无法合法的消除和解决。
四、 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角度解决此类困境
有一些法院判决在认定侵权时,认定的是酒店经营者侵犯了视听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而不是放映权[3]。虽然此种观点已经被逐渐否定,但是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经营场所提供互联网终端点播服务,点播的视听作品来源于网络,是他人事先“置于网络”的,不是酒店经营者提供的。根据王迁教授的观点,作品的“提供端”不是酒店经营者,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是“提供”行为,因此,酒店经营者不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那么,从此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大胆的为上述酒店经营者的困境提供一条路径:顾客在客房设备上点播来自于互联网APP的视听作品的行为,无论其属于本文第三部分列举的哪一种情形,都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个实现环节,应该归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而不是放映权。无论是顾客还是酒店经营者,都不存在侵权问题,既不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不侵犯放映权。而需要追究的则是,案涉视听作品的提供行为的合法性,即从源头来追究提供视听作品的APP运营者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是,则著作权人直接向APP运营者主张权利,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大海撒网式的去起诉酒店等经营场所。
此观点是否有法律依据?我们认为,从《著作权法》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看,应该可以得到支持。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
无论是《著作权法》,还是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特征,都是两个要素:1.将作品提供、置于信息网络;2.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等方式获得作品。即:提供+获得。这是实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提供”是前提,“获得”是结果。顾客在酒店客房中通过爱奇艺等此类观影APP点播视听作品的行为,属于“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浏览的方式获得作品的行为,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实现的一个环节。酒店等经营者只是提供了这个地点:客房和上网设备,但这也是顾客自己选定的地点,而谁提供的设备以及使用什么设备并不影响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实现。顾客的点播行为仍然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实现特征,也是视听作品提供者所期待的结果。
那么,这种理解是否与放映权相冲突呢?放映权的特征是,向公众“再现”视听作品。如前所述,放映权中“再现”的主体应该是被控侵权人。包括该被控侵权人“亲自操作”放映机等设备向公众播放视听作品,此视听作品可以是被控侵权人自己提供的片源(比如事先存储于硬盘、服务器等),也可以是来源于网络。被控侵权人自己操作播放供公众观看的时候,其不符合“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个特征,因此,即使其自己操作播放来自于网络的视听作品供顾客观看,也不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是放映权。但是,当顾客只是利用了经营者提供的上网设备“自己动手”点播来自网络的视听作品的时候,此时经营者并没有参与其中,其不是提供作品的主体,也不是点播动作的主体,因此,此种行为更符合顾客是“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浏览网络上的视听作品,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实现环节,不是放映权。那些酒店经营者提前购买了观影APP的VIP会员账号提供给顾客登录观看,也只是导致顾客在该观影APP上可观看作品的范围产生了改变,而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其行为的性质,不能因此导致经营者变成“再现作品”的主体,侵害放映权。那种将视听作品置于网络的提供端行为,与通过上网设备点播视听作品的获取行为,割裂开来分别归属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与放映权规制的做法,不符合立法本义,也不符合民众的普遍认知。
如此一来,则上述酒店经营者的困境将豁然开朗,得到彻底解决。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人,可以通过向观影APP的运营者许可获得收入,在被侵权时直接向未经其许可擅自将作品收录其观影APP中的运营者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获得赔偿。这也是打击侵权的源头,避免伤及大规模的终端经营者。这应该是理顺和整顿著作权商业秩序的一条有效途径。其好处无疑是各方受益,多方共赢:视听作品著作权人的权益并没有因此被减损;遍布全国数以万计的酒店等经营者得以合法而安心的提升服务品质而不必时刻担心被诉侵权;相关技术设备的生产制造业得以繁荣;法院也可以摆脱每年大量的此类批量维权案件的堆积,减轻案件负担。
当然,此种观点目前尚未查询到相关的判例支持,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以及实践的检验,甚至需要司法解释的支撑。本文只是提供一种思路。
参考文献
1.王迁:《论提供互联网点播终端服务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2.王晟:《浅析酒店行业侵犯著作权的难点:放映权亦或信息网络传播权分析思路 ——以著作权人代理为视角》,https://zhuanlan.zhihu.com/p/589533810
3.倪贤锋《私人影院擅自传播电影作品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还是放映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940364059528381&wfr=spider&for=pc
[1] 经查询裁判文书网以及“企查查”,目前以“宁波声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苏州市奋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为原告,在全国各地法院以“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放映权纠纷“为案由,提起针对提供投影仪等互联网终端点播设备客房服务内容的酒店“的批量维权诉讼案件,数量达到二千多件。此类案件已在酒店行业引起强烈反弹,福州的酒店行业经营者甚至到政府门口拉横幅表达诉求。
[2] 《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点播影院,是指在电影院和流动放映活动场所之外,为观众观看自选影片提供放映服务经营活动的文化娱乐场所”,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点播院线发行的影片,应当依法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其在点播影院放映的授权”。此规定显然与酒店行业不适用。
[3] 如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2民初691号“宁波声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福州市仓山区凯纳斯酒店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中即认为被告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