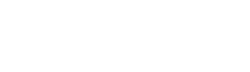知识产权保护:从中间商处进行坚决阻击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另一种思路
知识产权保护:从中间商处进行坚决阻击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另一种思路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杜昌敏
内容提要: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都分别规定了合法来源抗辩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缺陷,法官对于合法来源认定标准的混乱,导致经营侵权产品的中间商所承担的侵权责任偏轻,导致终端市场上依然是假冒、盗版横行,知识产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不妨采取另一种思路,“治乱用重典”,对合法来源抗辩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造,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中间商在购进产品时对产品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履行必要的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
关键词:知识产权 侵权诉讼 合法来源 抗辩
一、引言
我国从1982年制定颁布《商标法》、1984年制定颁布《专利法》到1990年制定颁布《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之后,从1990年代起,经历了多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美国谈判代表梅西的一句“我们是在与小偷谈判”,令中国人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泛滥及权利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力度疲弱感到汗颜。但毫无疑问,中国通过不断的立法、修法,加大执法力度和打击强度,二十多年来,知识产权的保护状况已经得到了不断的改善。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更是将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但是,毋庸讳言,即使官方所公布的各项数据体现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发布两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得到了很大改善,从民事、刑事、行政等各种途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成果丰硕,打击力度大大增强。但从常年从事知识产权诉讼业务,尤其是侵权诉讼业务的法律从业人员看来,知识产权保护虽然是不断在进步,但市场上依然是假冒、盗版横行,侵权行为是打过一茬又现一茬,知识产权的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这从这两年来在福建区域乃至全国范围所不断掀起的大批量的如北京网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影视剧侵权案、广东中凯公司影视侵权案、奥特曼形象侵权案、彪马商标侵权案、KTV音乐作品侵权案等等,可见一斑。官方的数据与现实中的直观感觉形成了一个反差。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本文认为,这与法律制度设计上对于经营侵权产品的中间商所承担的侵权责任偏轻有很大的关系。上述国务院《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三、战略重点:(13)修订惩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法规,加大司法惩处力度。提高权利人自我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有效遏制侵权行为。其中,应特别关注“提高侵权代价”这一点。因此,对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的中国来说,宜“治乱用重典”,对于我国三大知识产权法律——《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侵权诉讼中的合法来源抗辩制度及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进行重新设计。下文分项述之。
二、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现有法律规定
(一)、关于中间商:
一个包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从生产制造到终端使用、消费,其必然要经历几类不同的市场主体:生产者――经销商――零售商――消费者,这处于交易链中间、起商品流通媒介作用的“经销商”和“零售商”,就是整个生产、流通环节的“中间商”。中间商在市场流通、交易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间商既是商品的购买者,又是商品的销售者。其盈利来源于“购买”与“销售”之间的价差。因此其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也显得十分复杂。
(二)现行法律对于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规定
我国现行三大知识产权法律——《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都有关于侵权诉讼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条款。合法来源抗辩当然是针对中间商而言。上述三大法对于合法来源抗辩的规定各有不同。《专利法》第七十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从以上条文可以发现,三大法对于合法来源抗辩制度所确定的合法来源的界定、归责原则、法律责任都有所区别。
《专利法》确定的构成合法来源抗辩条件是,中间商主观上是“不明知”,客观上能证明其有“合法来源”,承担责任的情形是只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商标法》的规定的则是,中间商主观上“不明知”,客观上能证明其商品是“合法取得”的,与《专利法》不同的是,在字面上,其多规定了一个条件,即“能说明提供者”,承担责任的情形与《专利法》相同。实际上,“合法来源”本身就要求能说明提供者,否则就是没有合法来源。上述两法的规定,所确定的实际上是一种无过错的归责原则。中间商既然主观上“不明知”,即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又能提供合法来源,也无过错,但仍然要被认定为侵权,仍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法律责任。这已经体现了对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
与上述两法有较大区别的是《著作权法》的规定,其中间商并不是通常理解的“经销商”或“零售商”的概念,而是基于著作权的特殊载体相对应的“发行者”和“出租者”,发行和出租的产品是“复制品”。该条文并没有如上述两法正面规定合法来源免责,而是规定不能提供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那么,我们只能进行反向解释,即当发行者和出租者对其发行或出租的复制品能提供合法来源时,即不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其已经不再以是否明知为前提条件。另外,在承担法律责任方面,没有区分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两种责任方式。按条文字面的反向解释,即能提供合法来源时,即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包括停止侵权的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责任,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意味着认定其发行、出租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作品复制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这显然与《专利法》和《商标法》大不相同。这种不同也显示了《著作权法》的上述规定显得模糊不清,存在立法上的缺陷和不完善。
三.司法实践中对于“合法来源”的认定
上述三大知识产权法律只规定了中间商提供合法来源的责任承担,但是,对于什么是“合法来源”,如何认定“合法来源”,构成“合法来源”的条件是什么,都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界定,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各级法院对于认定合法来源的标准很不统一,甚至是达到了混乱的程度,这也给被控侵权的中间商们逃脱赔偿责任找到了很好的突破口,使得权利人打击侵权维护权利的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司法实践中对于“合法来源”的认定标准,相对一致的看法是,合法的进货渠道,正常的买卖合同,合理的进货价格,这三者构成了合法来源的主要构成要件。但是,对于被控侵权的中间商对这些合法来源要件的举证要求,却很不统一,宽严差别很大。如有的法官会要求提交进货的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生产商的营业执照等,这是从严的标准;有的法官可能只要求提交进货单,付款凭证;甚至有的法官认为,只要被控侵权的产品上已经正常标注有生产厂家并且该生产厂家是合法存在的,就应视为有合法来源。近年来,从宽认定合法来源标准似乎有越来越扩大化的趋势。
关于合法来源的立法本意,应当是从规范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出发,赋予中间商更多的对于产品上的知识产权进行合理注意的义务,同时,也便于权利人从源头上打击侵权。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合法来源认定标准的混乱,大大削弱了这个立法本意。
四、从中间商处进行坚决阻击的理由
绝大部分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最终都是要经由零售商面向最终端的使用者、消费者进行公开销售。这成了权利人寻找侵权产品的最重要也最方便的途径。只要找到了侵权产品,当零售商为了免除赔偿责任而提供其产品的合法来源时,权利人即能顺此通道最终找到侵权的源头――生产者,从而准确地进行打击。这是一般的思路。这种思路固然是正确的,打击侵权,当然要打击其侵权的源头,只有把源头消灭了,才能杜绝公开市场上的假冒横行。
但是,现实情况却给这种固然正确的思路大泼冷水。这种思路贯彻到现实的打击侵权中,收效却总是大打折扣。在零售商的公开市场上,侵权产品如同韭菜,割过一茬,又长一茬。中间商们也从来没有吸取承担侵权责任教训的想法,只要有利可图,侵权产品照卖不误。因此,历次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对话,中国市场的侵犯知识产权泛滥总是成为美国人的话题。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和理由:
(一)如上所述,现行法律对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法来源认定标准的混乱、从宽认定的趋势,导致中间商的侵权违法成本低下。只要提供了合法来源,中间商们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是进货时明知或应当明知产品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一旦诉讼,其照样声称不明知,而权利人对于中间商的主观状态是很难举证的。这种制度设计,无异于变相地纵容中间商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
(二)零售市场,是侵权产品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后一个环节。生产者的所有利润,最终都要通过经销商、零售商来为其实现。因此,直接打击生产者这个侵权的源头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能够设计一种制度,在为其实现利润的中间商处对侵权产品进行强有力的、彻底的阻击,让生产者即使生产出侵权产品,也没有中间商敢于为其进行销售,则侵权产品将无处容身,市场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净化。
(三)权利人从零售市场寻找侵权产品,进行证据固定,打击零售商,是最便捷、维权成本最低、收效最快的一个途径。
五、对合法来源抗辩制度进行适当改造
国务院《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已经提及“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如何把这句战略性话语化为实际行动,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谋略。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三大知识产权法律中所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制度及司法实践中对合法来源的认定标准进行适当改造和统一界定,是最便捷有效的办法。
首先,对于“合法来源”的内涵中,除了原有的合法的进货渠道,合法的买卖合同,合理的进货价格这三大要件外,加入赋予中间商对产品知识产权的合理的审慎的注意义务。即,中间商应建立起完善的进货审查制度,在购进产品时,应当对产品是否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进行合理的审查,当然这种审查并不必然要达到很专业的程度,其可以通过要求供货商随货提交涉及产品知识产权的权利证书、权利许可文件等,中间商只要审查这些随货文件即可。这可以排除掉大量的侵权产品,因为侵权产品必然无法提供相应的权利证书、权利许可文件等。
当然,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在对中间商的审查注意义务的要求上也应有所区别。专利权,因其体现的是某种技术方案,而这种技术方案具有其专业性,并且单从产品本身往往很难看出,当生产者、供货商没有主动声明和提供其专利权利证明文件的情况下,要求中间商对此进行审查和注意义务,显然不大现实。因此,对于专利法上的合法来源,对此可以不做强制要求,但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或经过媒体充分曝光,或经过生效判决确认的,中间商仍然负有审查和注意义务。否则,中间商将不得以合法来源进行抗辩。
而对于商标来说,只要产品上印制有商标,中间商无需专业技能就能看到,其就应有义务审查该产品上的商标权利状况,有义务要求生产者、供货商提供产品上所使用的商标权利文件。这种审查应当是轻而易举的,并不会增加中间商多少交易成本和交易难度。如果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则中间商也不得引用合法来源进行抗辩,而要承担包括赔偿损失在内的全部侵权责任。
但对于著作权来说,情况就显得复杂。因为著作权权利的产生与专利、商标不同,其在作品完成就自动产生,并无需经由登记发证程序。因此,一个产品上是否存在某种著作权,以及某个复制品上署名的著作权人是否真实,将很难判断。因此,在著作权方面,不能一刀切地要求中间商负担这种审查和注意义务。因此,对于著作权方面的合法来源的规定上,可以增加“不明知”作为中间商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如,对于某些已经很知名的作品,中间商属于“应当明知”著作权人的情况下,其即应承担相应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如迪士尼作品及其角色形象、奥特曼的作品及人物形象等,以及某一时期流传很广、全国热播的影视剧作品,即可推定中间商“应当明知”。如果中间商在“应当明知”的情况下,仍然发行和出租侵权产品,即可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当然,这种审查和注意义务只要达到必要和合理的程度即可。这种义务并不必然增加中间商的太多的交易成本和障碍,只要中间商建立起完善的进货审查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下去,将成为一种习惯。
其次,对于合法来源三大要素之合法的进货渠道、合法的买卖合同、合理的进货价格的审查,应当采统一的从严标准。如产品有合法存在的生产厂家,在公开市场上从合法的市场主体进货,有相应的进货凭证,买卖合同,正规的商业发票,与市场平均价相近的合理价格等。如不能举证,则应认定为来源不合法,即应承担侵权的全部法律责任。
从中间商处对侵权产品进行坚决的阻击,让生产者没有侵权的土壤,或许会大大改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状况。当然,上述做法必然会牺牲市场交易的一部分效率,但当效率与公正相冲突时,当仅仅牺牲一部分效率即能换来更多的公正时,我们只能选择公正优先。何况,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依然形势严峻时,何妨“治乱用重典”呢。
参考文献:
1、 郑成思,《知识产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
2、 杨帆,《知识产权合法来源的认定》, http://www.yzlegal.com/showart.asp?art_id=102
3、 郑之平,《使用侵权复制品的法律责任》,http://www.cipnews.com.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07
4、 祝建军,《专利法中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司法运用》,http://www.cqvip.com/qk/97762X/200806/27602750.html
5、 张广良,《.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
作者联系方式:杜昌敏,13809505925,dudalvshi@163.com